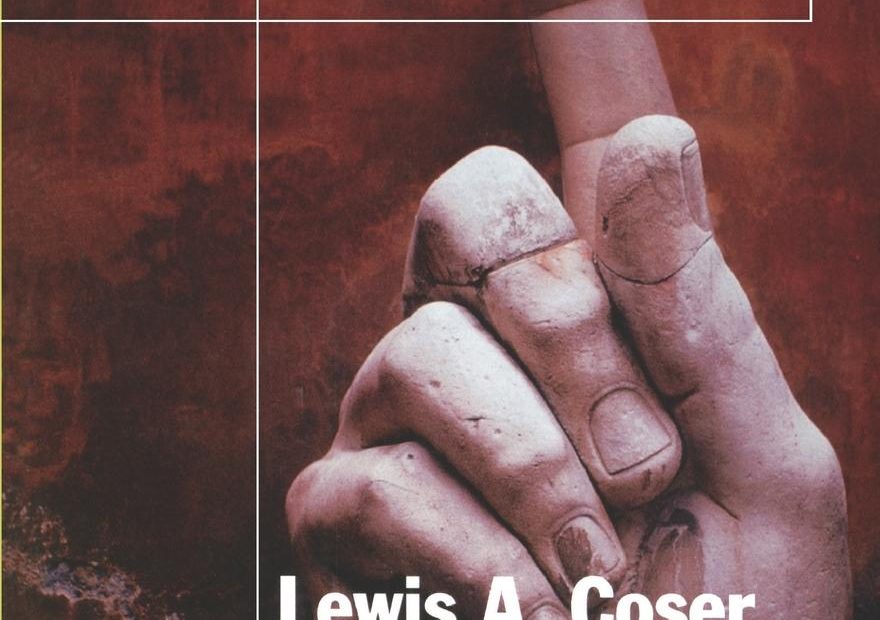政治就像一个风姿卓越的荡妇,知识分子历来都难以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
有的知识分子总想把她骑在自己胯下,驾奴她朝向自己理念的高潮前进,但最终反而不仅玷污了自己,往往又使政治以灾难告终;有的知识分子不断的和她调情,暗中引导着她走向正途,然而稍有不慎就落入她的技俩之中;还有一种知识分子和政治发生了“亲密接触”,开始以为自己拥有了她,最终证明不过是被她所玩弄;当然也有人从来就对她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而且不断指责她的“堕落”,这种知识分子是真理和正义上的“卫道士”;也有知识分子不安于与政治的包办婚姻,细数这位夫人身上的每处丑陋时,同时总不免对别的女人奉上言过之誉。
这几种对政治多情的知识分子就是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的《理念人》所概括的五种“理想型”知识分子。

哲学王
第一种是掌权的知识分子,他的原型是柏拉图的“哲学王”,柏拉图或许是第一个相信哲学家掌权能使国家和个人都趋于正义,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个。历来就有许多人“重温着柏拉图的梦想——尽管他们谁也没有机会把它变为现实”,因为“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和政治常规化的时期,国家事务显示出对知识分子争取政治优势的努力抵制”。但是,科塞说,“革命时期却可能为他们提供获取国家权力的机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俄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以及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那些“国父”们就是例证,然而“除了最后一种情形外,知识分子涉入政治领域,通常都是以灾难告终。”
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成员虽然大部分不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在其中都扮演着领导角色。他们是一群被就旧制度排除在权力之外的人,启蒙运动使他们“努力以理性和自然为根据,以批判的态度重新评价被人们所接受的观念和假设”,在这些知识分子掌权后就“想遵照理性和自然道德的指示重建法兰西”。雅各宾派决心与历史决裂,他们深知符号对于人的威力,于是砸碎了传统的历法、节日、服饰、称呼、街名等,目的在于扫清走向理性和道德的千年盛世之路。“由于渴望用高尚的罗马人和斯巴达人的形象来振兴法国的公民精神,他们试图用法令把博爱和友谊制度化,用立法来落实道德。”雅各宾派成了拯救世人灵魂而实施酷刑的良心审问官,他们那个为之奋斗的高尚目标成为了恐怖、独裁的合法性借口。
同样的覆辙也在俄国革命中上演。不同的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中的知识分子大多是“职业革命家”。列宁相信,要把俄国工人自发的工会意识转变为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政治斗争必须由革命的知识分子来领导,布尔什维克这个纪律严明近似宗派的政治组织就是俄国革命的先锋队。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和雅各宾派一样按照自己的理想愿望重建俄国,同样的恐怖统治,同样的暴力手段,使得他们的国家理想成为一个遥遥无期的明天。
这些自高自大的知识分子试图用法令重建社会和人格,无论是雅各宾派还是布尔什维克,无论在革命初期是人道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或是进步分子,一旦他们大权在握,一旦知识分子由批评者的角色变成独裁者的角色,他们就成了无情的杀人犯。
智囊团
第二种向政治调情的知识分子科塞把他们比喻为从政治“内部穿孔”。知识分子在看到革命时机尚未到来或者革命希望破灭后,转而考虑实际政治的迫切要求,他们“通过变成心腹人物、王权背后的权贵,慢慢按照他们的愿望改造现实。”从霍布斯到凯恩斯历来就不乏个别知识分子影响到政治决策之人,而其中最成功的要数英国的费边主义者。
费边主义者并不像那些革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主义者,鼓吹彻底推翻现有的阶级秩序,他们反对目前的社会秩序,但又强调他们与当权者的分歧只是眼前手段上的差异而非终极目标上的不同,从而打消了中产阶级的戒心又渐进的实现了社会改革的目标。科塞评价到,“费边主义者从权力大厦的内部穿孔过去,努力利用里面的居民曲折地达到了他们的很多目的。他们没有在英国创立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但为后来福利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费边主义者被马克思正统称为机会主义分子,正统的马克主义者都宣扬革命的理论,而反对和资产阶级同台竞争,然而事实证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最终败给了改良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在与资本主义比拼中彻底失败。
与费边主义者在英国的“内部钻孔”战略类似,大批对胡佛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失调而不满现行组织制度的知识分子,纷纷涌入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政府部门,力图改变他们时代的社会和政治氛围。这些年轻的新政知识分子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重要影响。
然而费边主义者和新政知识分子有重要的不同,“费边主义者能够为政治而生存,而不必靠政治吃饭,是因为他们经济独立,不必依靠政治带来的收入”,新政改革者中的许多人热衷于权力积聚,从而把自己搅进了官场之中,“知识一套上追求权力这个重轭,它就会失去其本质特征,必然变成辅助性的了。将知识套在权力的战车上,也就阉割了它。”
鼓号手
第三种知识分子帮助权力进行合法化,他们在旧的意识形态不能维持现行秩序时,他们或者为旧秩序提供新的合法学说,或者创造新的意识形态为新政权提供合法化基础。前者犹如英国的伯克、法国的夏多布里昂、德国的亚当·穆勒、美国的萨姆纳等保守主义者,后者犹如拿破仑时期的思想家和波兰的修正主义者。科塞着重讨论的是为新权力建立辩护体系的后一种知识分子。
拿破仑年轻时代就向法国当时知识分子大献殷勤,他们协助拿破仑掌握国民公会军队指挥权尽了不少力,拿破仑也以进入法国国家科学院为荣,他签署军告时也时常署以“总司令、科学院院士波拿巴”,使法国当时的知识分子们把拿破仑当作了未来的哲学家国王。拿破仑发动政变后,这些“思想家”帮助起草了既不自由亦不民主的“共和八年宪法”,但拿破仑最终与罗马教皇恋爱了,而抛弃了知识分子。
在波兰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中,哥穆尔卡站在修正主义知识分子一边,他成了知识分子的英雄。然而在哥穆卡尔上台清除了斯大林主义的死硬派后,修正主义知识分子遭遇了同样的清除。“当修正主义者的听众慢慢消失时,他们无力抵挡掌权者的要求,只能选择或是适应现实,或是退出公共场合。”曾经攻击旧政权为新政权合法化立下汗马功劳的年轻知识分子就这样遭到了权力的又一次玩弄。
批判者
第四种则是权力坚定的批判者,这种知识分子“无需经历幻灭后才相信权力和知识间有着长期不和谐的关系。他们从一开始就视自己为社会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如果必要的话,他们要以长期备战的状态进入政治疆场与那些掌权者厮杀。”美国那些怒不可遏地反抗丑恶奴隶制的废奴主义者和法国德雷福斯运动反对让真理屈从于国家理由的知识分子就是这一类人。
美国的废奴主义者并不寄托于获取政治权力或进入官场,也幸好他们不追求权力才获得极大的成功,因为如果他们掌握权力,同第一种“真理信奉者”一样会冷酷无情地滥用权力;从事这种事业也不会给废奴主义者个人带来社会地位或其他报偿,反而自身的安全常常受到威胁。“事实上,废奴主义者的行为深深根植于道德上的罪孽干,因而他们的政治是一种调动全部人格服务于非个人目标的良心政治。”
“德雷福斯事件”则是一场正义和秩序之间的斗争。反对德雷福斯案重审的一方是维护现存制度、集体纪律和民族利益的知识分子,他们主要来自巴黎的上策或是中上层;而支持德雷福斯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人,他们“对理性的信仰要高于国家的利益,即使它有损于安定团结和社会秩序。对普遍观念之有效性的信仰,以及捍卫这些观念的献身精神。”因此,科塞说“德雷福斯事件”是近代知识分子史的一个分水岭,“知识分子”,一词现今的涵义,无论褒贬,都来自于它。但这场争论至少证明了“以公众舆论力量为后盾的知识分子能够使当权者就范。尽管有司法障碍,正义还是胜利了。”
崇外人
最后那种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总是把目光投向国外,寻求解决国内问题的良方。“当知识分子与国内的政治趋势格格不入时,他们倾向于到国外寻求更和谐的状态。”这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典型的症状。
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崇华崇俄,大萧条时代的英美知识分子亲苏,以及60年代法国的知识分子又在崇华。“当西方的社会弊病达到顶峰时,俄国神话便有了充分的支配力,但当西方社会生活重新恢复了常态,这种力量就减退了。”每当国内处于变革时代,总把某个外国构建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从中观照体会到自我缺憾、焦虑不安与变革的冲动。
然而,这种崇外症“实际上变成了另一些国家而不是自己国家的权力机构的合法化制造者”。就像我们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时,自身却不断在“自我东方化”,即中国也在不断地把西方人所认可的中国形象强化后又向西方展示。
总之,一旦知识分子染指政治,无论是作为政治的掌权者、智囊团或是鼓号手都遭遇到官僚化的永恒难题。掌权者的知识分子必须“建立官僚制度来实施他们的计划,而正是他们建立的官僚机器限制了他们进一步的改革。”因此,正像阿伦特所说,革命的结果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不断革命。智囊型的知识分子要么追求自主而放弃政治,要么最终成为决策者官僚机构中用自己知识和技术盲目维护制度安排的温顺专家,一个和普通公务员没有多大区别的政治政策的执行者。为权力建立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也难以逃离官僚化的魔掌,布哈林那个讥讽苏联官僚化的笑话或许很确切,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母权制、父权制和书记制。
五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中,科塞虽然赞赏费边主义者们在英国所取得的成功,而实际上,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立身于政治之外,保留独立的批评精神,正如牛虻一样时刻刺激着当政者的神经。然而,随着知识分子越来越被同化于吸收到体制之中,大学、研究室、政府、文化产业、基金会等机构,这些机构也无不有着官僚化管理模式,在自由职业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稀有动物的今天,是否意味着知识分子的终结?
一篇旧文,贴过来支持人类与社会专题